翦伯赞、金岳霖、王世襄……燕东园满葬着一部知识人的精神图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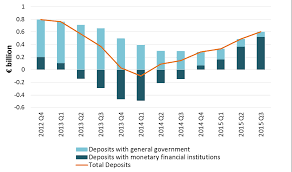

为何是燕东园
在中国现当代史上,冯至、何其芳、陈梦家、金岳霖是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,而他们都曾住在同一个地方,那就是别名“东大地”的燕东园。燕东园在北大东门附近,前身是明清时期的成府,据说在乾隆年间为太监营房,老太监们从宫里出来,死后就葬于此地。20世纪20年代,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买下这77亩地,建成了如今的燕东园。从此,一代代知识人与这里产生交集,这份名单包括但不限于游国恩、赵萝蕤、翦伯赞、洪谦等。
从20世纪20年代起,燕东园囊括了一批批杰出学人,但20世纪是革命与巨变的年代,知识分子也无法独善其身,他们的学识令人钦佩,他们在后半生不同的境遇,更令人唏嘘。
因此,燕东园是一个重要的坐标。但长期以来,缺乏一部专门挖掘其文化价值的专著,直到徐泓填补了这一空缺。打开此书,你既能发现王世襄的乐园、何其芳的读书会,也能看到冯至和杨晦“一个甲子的友谊”、周一良对于陈寅恪的愧疚,还有不能忘却的陈梦家与赵萝蕤。徐泓以扎实的笔触,书写了一部知识分子精神史,也抢救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过去。
燕东园由两个住宅区组成,中间以一座水泥桥相连,分别叫“桥东”“桥西”。作者徐泓的家就在桥西坡脚下。徐泓出身于学者家庭:她的母亲韩德常是幼儿音乐教育家、作曲家,谱写了《摇啊摇》《小小鸭子》《粗心的小画家》等曲子;她的父亲是中国计算数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徐献瑜。此公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,涉猎广泛,一直活到百岁高龄。
徐泓有志于写作,毕业后成为一名新闻记者,主张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和研究性。为了完成《燕东园左邻右舍》,她耗费数年,采访、调研了燕东园22栋小楼192个住户共211人。此书在叙事上有四层结构:其一是总介绍;其二写燕东园内已经被挂上“北京市历史建筑”牌匾的小楼;其三是九栋没有挂牌,但在燕东园(东大地)历史上不容忽视的小楼;其四是回顾作者自己的家庭,并对全书进行总结——这一部分也包括了后记。作者思路清晰,用一种建筑的方式搭建起了文本。通过96岁的胡路犀阿姨、原燕大宗教系主任赵紫宸先生的儿子赵景伦先生、“燕二代”关家麒等关键人物,作者不仅详细地整理出了燕东园及其前身东大地的住户名单,也打捞出不少与燕东园有关的逸闻趣事。
比方说:1950年之前,东大地有不少外籍住客。20世纪50年代初,朝鲜战争爆发,上头文件下来,燕大的外籍教师按照规定必须离开。于是在几乎同一时间,作者的家里突然多了好几件家具,“一对西式的高背床,两个西式柜子,还有几把造型别致的椅子,圆形椅面,带有一个略呈弧线的小椅背”,还有一条墨绿色的美国大兵用的军毯。
再比方说住在燕东园东区21号北半侧的金岳霖。他喜欢斗蛐蛐,燕东园的小孩传说他是斗蛐蛐界的高手。他家有几十个特大号的蛐蛐罐,有一个呈灰色、圆柱形,直径有十六七厘米,高十厘米,配套有小碟、小水槽。他给外人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,是他一辈子独身,只带着一名厨师住进燕东园,烤的面包挺好吃。
捎带在书中,徐泓还澄清了一件事。世人皆知金岳霖与林徽因是知己,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时,金岳霖写下挽联∶一身诗意千寻瀑,万古人间四月天。林徽因去世后不久,金岳霖就离开了燕东园。私下里有人说,这是因为林徽因不在了,金先生已经尽完了守候的责任。这是一个浪漫的讲法,但徐泓发现∶当时有几户人家和金岳霖同时搬出了燕东园,包括诗人何其芳。原来,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学部体制,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为四个学部之一,下设七个研究所。这些学者随工作调动,被调至各所任职。195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迁至建国门内贡院一带办公,这些先生随之搬进城里安家落户。

金岳霖
在燕东园有世俗喜乐,
也有婉转悲哀
对于学问的执着,和日常交往中的人情味,是全书屡次着墨的两点。在桥西34号楼下,游国恩抱病修订《中国文学史》和对《离骚》的正文校勘工作。在教室授课时,身形瘦矮的他嗓音洪亮,对古典文学烂熟于胸,在课堂上能随意背诵,不差分毫。也是在燕东园,何其芳会在家里定期举办《诗经》讨论会。1956年上半年,游国恩作为特邀人选出席。据说何其芳曾向游老当面请教研究《诗经》有哪些参考书,游国恩不假思索,列出了几十种书目。
在燕东园,你能看到冯至、姚可崑夫妇,他们家“院门口和楼门口都有藤萝架,春天垂下清香的淡紫色花串,家里拿来做藤萝饼吃”;你也能看到住在桥东21号的林启武,他曾因直肠癌手术而被切除肛门,却奇迹般地活过100岁,并为中国羽毛球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。1952年手术后,他的肠胃改道,只能通过在腹部切口造瘘排便。肃反时,有些会必须参加,他拿着一个充气的小橡皮圈去开会,垫在身下,裤子上经常是血。女儿那时候不懂事,埋怨父亲又带着“你的屁垫儿”,父亲说∶“NO!这是Donut(甜甜圈)!”
你还能看到王世襄。他是大收藏家、杂家,也是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。他住的王家花园紧挨东大地南墙,并非豪门深宅,更像一个大菜园子和数间房舍。就在这片花园里,王世襄种葫芦,养蟋蟀,遛狗捉獾,上课怀里揣着蝈蝈葫芦,下课胳膊上架着鹰。1936年,赵萝蕤和陈梦家新婚,借住在王家花园。某日深夜,他二人被嘈杂声惊醒,以为家中进来强盗,吓得不敢吱声。结果,这所谓的“强盗”就是王世襄自己!前一天夜半时分,他和同伴牵着四条狗去玉泉山捉獾,拂晓归来,料想学长夫妇早已入睡,便“拖狗带獾”翻墙入院。
而曾住在燕东园42号甲、出生于江苏吴江郑氏家族的郑芳,很多人知道她的丈夫是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周先庚。而她本人的才华、能力毫不逊色于丈夫:她是一个很有趣的妙人,在操持家务琐事的同时,竟能用半年时间自学俄语,所用的是一本很厚的用英文注释的俄语教材。生前,朋友们知道她语言学习能力很强,有一手好厨艺,又很喜欢养小动物。在她去世后,当70万字的《郑芳文集》出版,读者才知道无论是散文、小说还是人物速写,郑芳都能写得妙趣横生——而这些是她一边做家务带孩子,一边笔耕不辍完成的。
在燕东园,有甜蜜,也有沉痛。1952年,历史学家翦伯赞任北大历史系主任,住燕东园28号。十余载后,他被批判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改住燕南园。1968年12月19日,当工人杜铨师傅发觉不对劲,将门撞开时,翦伯赞与妻子平卧于床,穿新衣服,合盖一床新棉被。他们已经服用过量“速可眠”自尽了。
20世纪50年代,燕大西语系有五位著名教授,分别是赵萝蕤、俞大絪、胡稼贻、吴兴华、巫宁坤。十年后,除了巫宁坤和赵萝蕤,其余三人均在20世纪60年代死于非命。
1966年,陈梦家去世后,赵萝蕤与父亲赵紫宸同住在美术馆后街22号。赵紫宸在这个明末清初风格的两进四合院里住了29年,于1979年病逝,享年91岁。12年后,1991年,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全译本,译者赵萝蕤。她花了12年精心翻译这部作品。这一年,她79岁,一直活到了1998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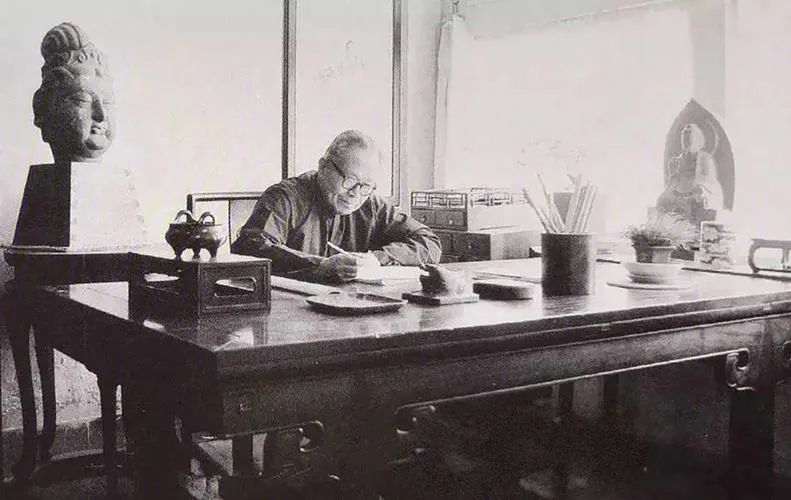
王世襄
此书无一字有怨愤
却处处可见执着
从抗战到改革开放,小小一片燕东园,经历了多次大时代的风浪。只不过,它也在走向自己的黄昏。2021年年底,北京市完成首批历史建筑示范挂牌,燕东园21-24号楼、31-37号楼、39号楼、40号楼入选并挂牌。往昔的热闹已成历史,这也是促成徐泓加快完成此书的原因。
《燕东园左邻右舍》既有史料价值,也是一部饱含人情味的故事集。讲述者如同历史导游,重返故地,走进旧楼,娓娓道来一个个门牌号背后的故事。作者的语调平和、熨帖,既不焦躁,也没有渴望煽动人心而产生的功利感。此书出版以后,我注意到一种声音,认为此书是精英写作,与普通人无关。这个观点是值得继续思辨下去的。
首先,在表面上看,这的确是一本记录精英的书。燕东园内居住的多是高校学者,他们中不乏社会名流。从社会地位上来看,他们是事实上的精英。但是,读完整本书,我所感受到的并不是精英写作常见的炫耀与粉饰,而是作者对一个个具体之人的认真追索,以及在这份耗费多年心力的追索之上,对于历史现场尽可能的去伪存真,和对于历史悲剧的婉转反思。
此书无一字有怨愤,却处处可见执着。在有限的出版尺度之内,作者尽可能地记录了一代学者在历史大变局中的选择与争议。作者不去评判那些选择的好坏,而是恪守自己作为记录者的分寸,用人物生命的厚度,代替掷地有声的论断。
在与许知远等人对谈中,徐泓直言:“在做这些采访的时候,我是在与遗忘抗争……作为一个社会,作为一个民族,作为一个群体,如果遗忘,而且是故意地、选择性地遗忘它所受的苦难,那就非常可悲了。一旦遗忘,同样的苦难就会发生第二次、第三次。”
读完全书,回味陈梦家、赵萝蕤、翦伯赞等先贤的往事,我才更了然作者所说“不遗忘”三个字的分量,也明白她为什么要在当下完成这本书。这是一部知识人的精神图谱,也是以小见大、关于一段崎岖年代的痛史——它不应该被遗忘。正因如此,作者不仅是为知识分子而写,她也在为有骨气、有信仰、心存善念与求真精神的人们而写。
作者| 默存 编辑|罗皓菱
